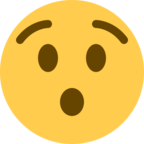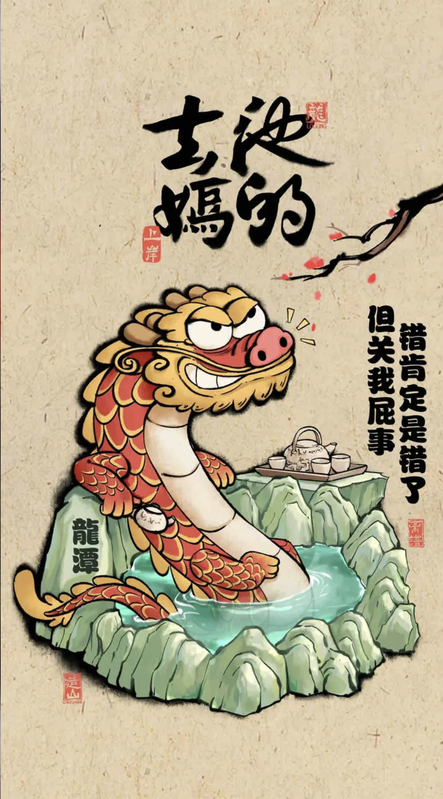先说几个比较近代的
转:
扬州十日 (1645年5月20日至29日)
事件经过:
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南下,兵临扬州城下。当时镇守扬州的是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是一位忠勇的将领,他拒绝了清军的多次劝降,决心与扬州共存亡。他带领城中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然而,由于兵力悬殊,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扬州城在坚守数日后,于5月20日被清军攻破。史可法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害。
为了报复扬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并恐吓其他地区的反抗力量,多铎下令屠城。从5月20日到29日,清军在扬州城内进行了长达十天的烧杀抢掠,史称“扬州十日”。
据幸存者王秀楚所著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屠城期间,““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无数平民百姓惨遭杀戮,许多妇女不堪受辱而自尽。
死亡人数之争:
关于扬州十日的死亡人数,历史上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八十万之说: 此说法主要来源于《扬州十日记》的记载,书中提到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八十万余”。这一数字在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学者质疑与考证: 近现代不少学者对“八十万”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根据明末扬州的行政区划和人口规模,当时城中人口,即使加上外来避难的民众,也很难达到八十万之众。有学者考证,当时扬州府总人口约为一百万,而扬州城内的人口容量至多在二、三十万左右。因此,八十万的死亡人数可能存在夸大,意在揭示屠杀的残酷性。
较为可信的估计: 尽管具体数字难以精确,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扬州十日的屠杀极为惨烈,死亡人数巨大。综合各种史料和人口学的分析,较为保守和可信的估计是,遇难人数在十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二、三十万。无论确切数字为何,这都是一场针对平民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
嘉定三屠 (1645年7月-8月)
事件经过:
扬州失陷后,清军继续向南推进。清廷颁布的“剃发令”传到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后,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愤慨。嘉定人民在侯峒曾、黄淳耀等士绅的领导下,组织义军,据城反抗,拒绝剃发。
清军派遣吴淞总兵李成栋(原为明朝降将)率军攻打嘉定。嘉定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抵抗。然而,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嘉定城于7月4日被攻破。为了惩罚嘉定人民的抵抗,李成栋下令屠城,进行了第一次屠杀。
不久之后,城外的幸存者和附近的义军再次组织起来,光复了嘉定城。李成栋闻讯后,率军返回,再次攻破嘉定,并进行了第二次更为残暴的屠杀。
8月,原南明将领吴之藩率部反攻嘉定,但未能成功。清军随后对嘉定及其附近乡镇进行了第三次扫荡式的屠杀。这三次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死亡人数:
关于嘉定三屠的死亡人数,同样存在不同的记载:
据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记载,城内外死者“约凡二万余人”。朱子素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记载被认为是较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另有一些史料和说法称死亡人数远高于此,有“五六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说法,但这些说法的来源和可靠性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综合来看,两万余人的遇难数字是基于亲历者记述的相对保守和可信的估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城内外的死亡人数,并未完全涵盖三次屠杀中在周边乡镇被杀害的民众。嘉定三屠的残暴性,不仅在于死亡数字,更在于其反复多次、带有报复和灭绝性质的屠杀行为。
转: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死亡人数考证
1900年庚子拳乱期间,沙皇俄国在清朝东北边境制造了两起震惊中外的屠杀事件: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这两起事件是沙俄趁火打劫,武力驱逐并屠杀当地中国居民的野蛮行径,造成了数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由于当时局势混乱,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两起事件的确切死亡人数在不同史料中记载各异,但综合来看,遇难者总数约为7000人。
海(hǎi)兰(lán)泡(pào)惨案:约5000人遇难
海兰泡是中国传统称谓,位于黑龙江左岸,与右岸的中国城市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隔江相望。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海兰泡被割让给俄国,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到1900年,城中及周边仍居住着大量中国商贩、工人和居民。
惨案经过:
1900年7月,随着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兴起及清军与俄军在黑龙江的零星冲突,海兰泡的俄国军事当局以此为借口,对城内的华人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7月16日至21日,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被俄国哥萨克士兵强行押解到黑龙江边,俄军逼迫他们渡江返回对岸。
然而,当时江水湍急,俄军并未提供任何船只。他们用武力将人群赶入江中,对试图反抗或在水中挣扎的民众则用枪射击、用刀砍杀。最终,绝大多数人惨遭溺毙或被杀害,黑龙江江面上一时浮尸遍野。
死亡人数考证:
关于海兰泡惨案的遇难人数,史料记载不一,存在多种说法:
中方记载: 当时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报告称有五千余人被杀。后来编纂的《瑷珲县志》也采用了“五千余”的说法。吉林将军长顺则报告称死亡人数在五千至六千人之间。
俄方记载: 俄国方面对此事的记录数字普遍偏小。例如,有俄国学者记载为3000至4000人。
综合认定: 目前,历史学界普遍采信中方的记载,认为海兰泡惨案的遇难者人数约为5000人。
江东六十四惨案:约2000人遇难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以南,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根据《瑷珲条约》,此地虽划归俄国,但条约明确规定,居住在此地的中国人“永远居住,仍著中国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因此,这里在法理上仍是中国居民的世居地。
惨案经过:
在制造海兰泡惨案的同时,沙俄军队也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采取了同样的灭绝政策。俄军包围了村庄,焚烧房屋,将居民全部驱赶至黑龙江边,强行渡江,并对反抗者予以射杀。许多未来得及逃离的村民,包括大量老弱妇孺,直接被烧死或杀死在村中。
死亡人数考证:
江东六十四屯的死亡人数同样存在不同说法:
有史料记载,当地原有居民约为5000人,惨案后几乎被屠戮殆尽。
但更为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江东六十四屯的遇难者人数约为2000人。
转:南京大屠杀:30万以上华人遇难,平民与战俘皆遭浩劫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在长达六周多的时间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根据战后两大国际法庭的权威判决,以及中国历史学家的长期考证,遇难者总数超过30万人。这些遇难者中,既包括大量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也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
死亡人数:30万之殇
“30万”这一数字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严肃的历史与法律依据。它主要来源于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并得到了大量史料的佐证。
南京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明确判定:“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这一判决是基于当时多方证据,包括幸存者证词、埋尸记录、现场勘查等作出的法律结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认定: 1948年,由同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也作出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的判决特别指出,这一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因此,20万仅是一个保守的、不完全的统计。
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 屠杀期间及之后,南京的慈善机构如世界红卍字会、崇善堂等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遇难者遗体。据不完全统计,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66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掩埋43,071具。这些有据可查的记录为大屠杀的规模提供了直接证据。
综合以上法律判决和历史证据,“遇难者30万以上”是中国官方和主流学界所持的立场,它代表了对这场浩劫规模的权威性认定。虽然国际上部分学者对此有不同估算,但两大军事法庭的判决至今仍是定义这一历史事件严重性的核心法律依据。
死亡人员成分:平民与战俘的共同悲剧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战俘)和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日军的屠杀是无差别的,无论军民,均未能幸免。
- 被屠杀的中国战俘
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数万名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官兵滞留城中。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已经放弃抵抗,成为战俘。然而,侵华日军并未遵守国际公约中关于善待战俘的规定,而是将他们视为“可耻的俘虏”,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屠杀。
典型案例:
草鞋峡大屠杀: 约5.7万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警和难民,被日军押至长江边的草鞋峡,以机枪扫射,并纵火焚尸,最后将骸骨投入江中。
幕府山大屠杀: 约2万名已经投降的中国官兵被集体屠杀于此。
鱼雷营大屠杀: 约9000余名战俘在此被集体杀害。
据历史学家孙宅巍等人的研究估算,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含战俘及已放下武器的士兵)数量约为7万至9万人,约占总遇难人数的四分之一。
- 被屠杀的无辜平民
平民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主要的受害群体。日军进城后,对普通市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淫掠。大量平民在街头、家中或避难时惨遭杀害。
屠杀方式: 日军的屠杀手段极其残忍,包括机枪扫射、刺刀捅杀、活埋、焚烧、砍头等。许多屠杀是随机和零散的,日军以杀人为乐,进行“杀人竞赛”。
受害群体广泛: 遇难者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据统计,日军在南京共犯下约2万起强奸暴行,许多妇女在被奸淫后即遭杀害。
安全区内的屠杀: 即便是在西方人士设立的“南京安全区”内,日军也频繁闯入,肆意抓捕青壮年并将其押出屠杀,安全区并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数据,由慈善机构收埋的15万余具尸体,绝大部分是零星被屠杀的平民。

 x1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