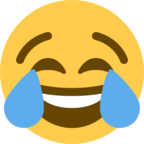文章来源: 押沙龙yashl 于 2022-10-09 14:11:4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被阅读 27623 次)A- A A+
这些天看了几本关于日本昭和时代的书,有点感想,随便说说。
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周围国家带来巨大伤害。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坚定地认为,日本才是受害者。
占领东三省、全面侵略中国、偷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结果日本才是受害者?
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不光英米鬼畜在欺负他们,就连中国也在欺负他们!他们被欺负得没办法了,才迫不得已含泪而战。在正常人看来,这简直是疯子的想法,可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就是这么想的。
01
先说占领东三省这件事。
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说了一句名言:“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而且,确保在满蒙的利益是日本人“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就得死。

松冈洋右
这听上去真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些地方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啊。邻居家的客厅怎么就成了你的生命线了,不让你在那儿打地铺怎么就冒犯你的生存权了?你家房子再小也不能搬人家客厅睡里啊?再说,日本人以前没有满蒙,没死;日本人后来没有满蒙,也没死;怎么偏偏在那个时候,没有满蒙就得死呢?
这段言论发表后,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位著名的自由派记者清泽洌,他就算了一笔经济账,认为满蒙没那么重要。
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主要利益就是南满铁路。清泽洌计算了一下,发现南满铁路每年给日本的收益是五千万日元。为了保护这个利益,日本调动关东军长期驻守,花费大量军费。此外,关于南满铁路的争执还使得中日贸易收到严重损害,而中日贸易每年总额是十亿日元。清泽洌提醒说:“把爱国心拨算盘的珠子算一算吧!”
那么,日本老百姓会听松冈洋右的呢,还是听清泽洌的呢?
想都不用想,当然听松冈洋右了。
从那以后,“生命线”、“生存权”就挂在了日本老百姓的嘴上。他们并不认为把别人的领土当成自己的“生命线”很荒唐,反而坚定地认为这是“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
02
所以,他们觉得中国欺负人。
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冲突焦点。日本坚持说,1905年清朝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中方不能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道线。可是张学良却开始修建平行铁路,这是在欺负日本人!
不许一个国家在自己土地上修建铁路,这本身就是荒唐的。而且实际上,清朝也并没有承认这一条款。“不得修建平行线”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要求,只在会议记录里提到了,并没有写到条约里去。即便按照日本学者自己私下里的说法,这也只是“条约的灰色地带”,最多属于外交争议。但是日本军方把它渲染成了天大的事情,说这件事让日本的“生存权”受到了严重挑战。
日本老百姓当然照单全收,叫嚷着要“惩罚中国的不义”。谁要是胆敢说什么“灰色地带”,就会受到万人唾骂。
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欺负人,日本是受害者。
在这种背景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事变是关东军自己挑起的,他们炸掉了一小段南满铁路的铁路线,然后拿来做侵略借口。日本内阁当然都知道这是日本军方没事找事,但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又愤怒又激动,变得极其狂热:难道能让中国这么随便欺负咱们吗?一定要惩罚他们!
结果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当时的日本内阁对军队的胆大妄为也很不爽,但是没人敢对老百姓说出真相。“铁轨是咱们自己炸的呀!”当时日本有暗杀政客的风气,要是哪个政客敢这么说,绝对是必死无疑。
只有个别学者说了点不同意见。比如东京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写了篇文章,说:就为了几米长的铁轨,占领人家整个东三省,这能说是自卫战吗?另一位教授吉野作造也说:这样占领别人的土地是不义之举,我们从小收到的教育不就是“渴死不喝盗泉之水”吗?怎么能要这样的土地呢?
结果大家群起讨伐。报纸发表批判文章《卖国教授、毒笔之主横田喜三郎逃往满洲》、《快快埋葬那些以大学为巢穴的国贼》。教授家里收到了好多谩骂信“去死吧!国贼!”,吉野作造在国外开会回来,都不敢上岸,怕被闻讯赶来的争议群众当场打死。
0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复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国际联盟组织了一个“李顿调查团”,来调查这件事。
李顿调查团当然知道这是侵略,但又不愿意太得罪日本,所以尽量和稀泥。它对中国做出了不少批评,要求中国对日本做出一定让步。这让中国人相当失望,鲁迅在《友邦惊诧论》里就说:“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
但是日本人看来,却完全不是这样。国联怎么会跟我们一伙?明明是他们勾结了中国,在欺负我们啊!
因为李顿调查团再和稀泥,最后也明确表示:东北是中国领土,“满洲国”不合法,国联不予承认。
在日本人看来,李顿调查团这简直是丧心病狂。《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正义之国,日本》,里面义正严词地说:“这是要剥夺自主国日本天赋的权利,在人类史上,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不正义之举!”报纸们还都痛批日本内阁是一群废物,任由李顿调查团欺负我们。后来,日本退出国联,大家才算消了一口气。
中国欺负我们,国联欺负我们,全世界都欺负我们。我们日本人是受害者,没招谁没惹谁却横遭欺负,所以我们只好含泪占领东三省,含泪在那里杀人放火——抗联欺负关东军,不反击行吗?
我们可能会觉得,日本人当时信奉丛林法则,觉得谁强谁有理。如果你这么想,就低估他们的自欺能力了。他们还真觉得自己占理,别的国家都在残酷无情无理取闹,只有日本是正义和高尚的。
全世界恐怕都很难理解日本的这套受害者逻辑,但是日本老百姓就是要这么想。
04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了。不用说,他们觉得又是中国在欺负日本。
日本老百姓一直觉得中国在欺负日本。比如中国爆发抗日学潮,抵制日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挑衅,就是“暴支”在欺负人。他们从来没有换个角度思考过,人家为啥要反对你,要抵制你?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么好,他们还要“抗”我们,这就是欺负人。
七七事变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耸人听闻的图片:“中国军队杀人了!这是咱们的死者!”老百姓不管真假,马上就叫起来了,呼吁要“膺惩暴支”!当时那么弱小的中国,设了多么多租界,被占了那么多领土,居然能跟“暴”联系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侵华战争是在一片喝彩声中开场的。
日本老百姓普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道德的,甚至是“国际主义”的。自我感觉良好。

日本宣传画,日本兵搂着的那个小胡子画的确实像汉奸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日本老百姓被欺骗了。但是他们其实也愿意受骗。你不骗他,他骂死你。比如九一八事变时期,《大阪朝日新闻》一度持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日本军部颇有微词,建议中日关系还是缓和处理。结果日本群众出离愤怒了。他们发起了“不买运动”,不买不买就是不买,谁买这份报纸谁就是卖国贼。结果报纸发行量3万、5万的不断锐减。主编撑不住了,只好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呼吁要“拯救东北三省水深火热的人民,建立满洲国”,还发动大家给关东军制作“慰问袋”,这下报纸发行量起死回生,打了个翻身仗。
老百姓就爱听这个,你让报纸怎么办?
说到底,就是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堕落了。当时日本有位地位尊崇的元老,叫西园寺公望。他权力相当大,可以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谁能当首相,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他的一个念头。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对日本老百姓的这种古怪心态也颇为不解。他说:日本百姓怎么会如此相信军部?他们怎么会支持一些明显荒谬的事情?
西园寺公望的结论是:日本的教育出了问题。
05
后来的历史不过是以前的翻版。
日本不断受欺负。蒋介石不肯谈和,是在欺负人;英国人通过缅甸往中国运送东西,是欺负人;美国人不肯续签《日美通商条约》,是在欺负人;美国不肯卖石油给日本,是欺负人……
反正周围的国家都在欺负人,只有日本不欺负人,结果被他们合伙欺负。日本提出出了一个所谓ABCD包围圈,认为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勾结起来,包围善良淳朴的日本。

日本战时宣传画:挣脱ABCD的枷锁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最后,日本含泪偷袭珍珠港,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人家脑袋上扔炸弹,按照日本报纸的说法,这不能算偷袭,因为“忍耐也有限度,一亿国民的积愤已经到了极点!”
日本人又敲锣打鼓地欢呼起来了,“驱逐元寇,神风起兮”,“举起和平的利剑,铲除邪恶,匡扶正义”、“消灭米英鬼畜”。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东京大轰炸和广岛原子弹。
06
但是,别看这么满腔义愤,一旦战败,他们转变的速度也快的惊人。
不久前还大声谴责米英鬼畜的《每日新闻》,日本投降后马上刊登谢罪书,为自己以往的谬论而道歉,保证以后洗心革面,再也不胡说八道了。
不久前日本漫画家加藤还在制作漫画,让一把刺刀插进半人半兽的罗斯福屁股上,说“彼奴等的死,就是世界和平的诞生日”,现在也转而歌颂美国大兵是“解放者”、“天降的礼物”。

漫画家转而歌颂盟军剪断了日本人民的枷锁
不久前还在发誓哪怕一亿玉碎,也要消灭麦克阿瑟侵略的读者,现在也转而写信赞美“麦克阿瑟将军”。有个县的12万人用八个月的时间,一人一针,绣出了一副麦克阿瑟像。
不久前还在课堂上赞美“大日本皇军”的日本教师,急吼吼地把课本上有碍字眼全部涂掉,转而赞颂美国的自由民主。由于变脸太过突兀,据说给很多日本小朋友带来了心理创伤,导致他们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小孩子怎么能理解大人的世界啊。
你看着他们傻,有时候他们又精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