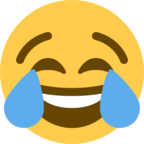我写了一首诗如下:
一树金黄入眼帘
空庭巨焰冷阑珊
小楼灯火阴处静
落叶纷纷自成圆
旧游不记昨昔欢
依稀仍是梦栏杆
小妹不识主人面
迎着宾客算酒钱
押韵的问题自然存在,不必赘言。但更关键的是,这首诗并非写实。那么,它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哪些?
那天我去的是“生日琶梯”,地点其实是一个电子游戏厅。庭院里有十余棵树,每棵都有两三层楼高,整树黄灿灿的,像巨大的火炬。但又不完全是火炬——火炬的颜色分层,而秋树的黄却匀净如染。
小楼并非古时木构,而是石灰水泥结构。霓虹灯虽闪,却不是高速路边那种大招牌。没变样的是游戏机和楼梯扶手。
根据叶嘉莹先生的观点,诗歌应通过意象的延展来传达诗人的情怀,使读者得以共鸣。但我私心里对这一说法略有保留。他日重读这首诗,我很可能记不起写作的缘由,甚至怀疑它是否出自我手。达于人,叶先生做得极好;但达于己,或许写实更为稳妥。
我曾尝试将“一树金黄”改为“十树金黄”,不妥当。因为当车拐入庭院时,确实是那一树最先映入眼帘,最为惊艳。至于“小楼”,改成“灰楼”或“水泥楼”虽更贴近现实,却失了诗意。“楼”这个词至今未变,成了语言的惯性。
“依稀仍是梦霓虹”虽贴近真实,却不押韵。只好写个日记记下。
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如今写诗的人少了。若写诗者众,必能琢磨出更多新兴娱乐风雅的表达方式,也就不必如此纠结意象的延展与连接。
但现实是,娱乐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若诗也如汪洋大海般浩瀚,诗人要从自身经验中写出一首具有意象延展的作品,读者若无类似经历,恐怕难以共鸣。